
内容简介
恰克‧ 帕拉尼克Chuck Palahniuk, 1962-出生美国靠近沙漠地带小镇,身上流有俄罗斯和法国裔的血液,恰克‧帕拉尼克小孩子时,和双亲去墓园探望祖父母的墓地,面对墓碑上的名字,询问他的姓Palahniuk要如何发音,他的母亲指着墓碑上祖父母的的名字,告诉他,就是他来自乌克兰的祖父和祖母的名字,帕拉(Paula)和尼克 (Nick),连起来念。所以也就是帕拉尼克。
他的祖父尼克‧ 帕拉尼克谋杀了他的祖母帕拉‧ 帕拉尼克后,带着枪准备将他四岁的父亲斐德列一起宰掉,但他躲在床底逃过一劫,他的祖父尼克随后用枪把自己的头轰掉。五十多年过后,他的父亲斐德列‧ 帕拉尼克在三结三离之后,因地方报纸上的「我爱红娘」personals,开始和年轻的女人唐娜约会,唐娜的前夫戴尔因为对妻子性虐待而吃上牢饭,假释后尾随斐列德和唐娜的车,跟踪他们,于他们过夜后要开车离去之时,开枪将他们双双射杀,然后将尸体拖回之前他们一起过夜的小屋焚毁。
大学主修新闻,毕业后怎么也找不到报纸当编辑,恰克‧ 帕拉尼克三十老几才开始写作,于1996年出版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斗阵俱乐部》(Fight Club),这是他所写的第二本长篇,是一本对出版社说FuckU的黑色幽默书,因为他们百般叼难、拒绝出版他的前作,而这本前作《隐形怪物》(Invisible Monsters)到了他成为畅销作家后又成了抢手货。《斗阵俱乐部》的第一版限量精装本并没有受到重视,但因为口碑和特殊的封面设计引发注意之后,不久则成为小经典的畅销书,随后好莱坞将它改编成电影。其畅销程度让他可以摆脱原本柴油车技工的蓝领阶级,买了一栋位居奥瑞冈州波特兰附近的农场专心写作,和一群古怪的朋友住在一起,以及一群鸡。恰克随后出的四本小说,皆混合了讽刺、喜剧、恐怖、真实与美丽,以及他独特的超现实黑色幽默。这些小说的内容一贯他让人咂舌的古怪离奇,包括有整本页码倒着排,描写宗教集体自杀一人独活,在波音747空中爆炸前在几万公尺的高中对着黑盒子讲述生命历程的《残存者》(Survivor)﹔截肢的时尚模特儿爱上变性人、跨越性别疆界线的公路小说《隐形怪物》﹔前医学院学生在餐馆假装痉挛无法呼吸以骗取一个拥抱或金钱的《窒息》(Choke)﹔以及去年出版,描写童谣杀人狂,被号称为21世纪恐怖小说文艺复兴的《摇篮曲》(Lullaby,around系列将于 2004年年初出版中译本)。但恰克却相当幽默而诚恳的说这些都是「浪漫喜剧」,都是有关男孩把女孩的爱情故事。今年八月底他将出版他的最新长篇,从女性口吻描写「昏迷状态」的《日记》(Diary),以及一本波特兰的旅行书《逃亡者与难民》(Fugitives & Refugees)。
问到他想成为怎样的人,他则模仿《斗阵俱乐部》里的口吻说:「个人上,我情愿被认为是一片美丽而独特的雪花。」而当年第一版的《斗阵俱乐部》,目前的抛售价则已经高达每本五百美元。
目录
有过这么本书 他俯身向前,他呼吸里是直接从酒瓶里灌威士忌的酒气。他嘴巴从不会闭紧。他蓝色的眼睛从来都半睁半闭。他一手拿了个盘起来的绳圈,那种老式的麻绳,金灿灿的像他的头发。黄得如同他的牛仔帽。是牛仔用的那种绳子,而且他讲话时直在我脸前摇晃手里的绳子。他背后是扇开着的门,有段楼梯往下伸入黑暗中。 他正年轻,小腹平坦,穿件白色T恤,脚上是棕色牛仔靴,带厚厚的跟儿。他头发在牛仔草帽下金灿灿的。一条皮带系住蓝色的牛仔裤,皮带上带个巨大的金属带扣。他瘦伶伶的白胳膊,晒成光滑的古铜色,就像每个牛仔穿的尖头靴子的尖儿。 他眼睛里蒙着细碎的血丝,他说要抓紧绳子,紧握不放。然后拖着那条绳子开始往下走,他牛仔靴的靴跟砰地砸在一级台阶上,然后是下一级,再一次重重地敲打木头台阶后,我们就进入黑暗的地下室。在黑暗的地下室,他拽着我,他呼吸中是威士忌的酒气,跟医生办公室里的棉球一模一样,在给你注射前擦酒精的冰凉触感。 又往黑暗中走了一级后,那牛仔说,“闹鬼地道之旅的首要规则,就是你不能谈起闹鬼地道之旅。” 我停住脚步。那绳子在我们之间仍松松的,像个揶揄的笑。 “闹鬼地道之旅的规则二是你不能谈起闹鬼地道之旅……” 那绳子,那粗纤维编结在一起的触感,猛地擦了一下我的手,差点滑脱。我仍站在原地,把绳子往回拽了一下,说:嘿…… 那牛仔在黑暗中说,“嘿,怎么了?” 我说,那本书是我写的。 我们之间的绳子紧了一下,越来越紧。 绳子拖住了那牛仔。他在黑暗中说,“哪本书?” 《搏击俱乐部》,我告诉他。 那牛仔往上倒退了一个台阶。他靴子在台阶上的敲击,听起来更近了些。为了看得更清楚,他把帽子往后压了压,两眼直对着我,眨得飞快,他呼吸里的酒气像加了啤酒的威士忌一样浓,像是对着一个呼气测醉仪,他说: “有过这么本书?” 没错。 之后才有了那部电影…… 之后才有弗吉尼亚的“四健会” 因组织搏击俱乐部而被搜查…… 之后多娜泰拉·范思哲才将刀片缝到男式时装中,称之为“搏击俱乐部款”。之后才有Gucci的时装模特裸着上身,眼睛涂得乌青,满身伤痕血迹斑斑绑着绷带在T型台上走秀。之后Dolce & Gabbana才在米兰肮脏的地下室里发布他们的最新男性风尚——光滑的1970年代衬衣印上大幅照片,军用迷彩图案的裤子和紧身、低腰款皮裤…… 之后小伙子们才开始用碱液或强力胶水在手上烧出吻痕…… 之后全世界的小伙子们才开始采取合法行动将名字改为“泰勒·德顿”…… 之后Limp Bizkit乐队才在他们的网站上打出标语:“泰勒·德顿医生建议服用有利健康的Limp Bizkit”…… 之后你走进“欧迪办公”商店购买粗制白色斜纹布标签用料时,才能在艾利包装盒(产品号8293)上找到个简单的标签,上面印着:“泰勒·德顿,造纸街420号,威尔明顿市,特拉华州19886)…… 之后巴西的夜总会才开始出现拳斗,有些夜晚年轻人才会一直打到死才罢手…… 之后《标准周刊》才开始宣称“阳刚之危机”…… 之后苏珊·法露迪的书《失信:美国男人的背叛》才出版…… 之后杨百翰大学的学生才开始为他们在星期天晚上彼此对打的权利而战,坚称摩门教的律法中并无禁止他们的“普罗沃搏击俱乐部”之规定 …… 之后犹他州州长的公子迈克·里维特才被控妨碍和平及在一家摩门教堂内非法经营搏击俱乐部…… 之后《洋葱》报 才披露了“缝被子协会”的内幕,说一帮老太太定期在一家教堂的地下室聚会,渴望“赤手空拳的纯手工缝制行动”,而“缝被子协会的首要规则是你不能谈起缝被子协会”…… 之后“周六直播夜” 才有了专题讨论:“‘像个女孩般搏击’俱乐部”…… 之后杂志和报社的编辑们才开始打电话,问在他们附近哪儿能找到一家典型的搏击俱乐部,这样他们就能派一位秘密记者前去写篇特写稿了…… 之后杂志和报社的编辑们才开始打电话痛斥、咒骂我,因为我坚称有关搏击俱乐部的一切不过是我的向壁虚构。纯属我的想象…… 之后全国政治卡通片协会才开始放映“国会搏击俱乐部”…… 之后宾西法尼亚大学才专门召开学术会议,学者们将《搏击俱乐部》细细切碎,将其与自弗洛伊德到软雕塑 再到阐释性舞蹈 的所有玩意儿搅和到一起…… 之后才出现无数量名为“性交俱乐部” 的色情网站…… 之后无数量美食评论才以大幅标题自称“咬嚼俱乐部” …… 之后Rumble Boys公司才开始在他们的男用整发产品,摩丝和发胶的标签上引用泰勒·德顿的“名言”…… 之后你走过各机场大厅,才能听到伪造的广播,传唤“泰勒·德顿……泰勒·德顿能否接一下白色礼仪电话 ”…… 之后你才能在洛杉矶发现各种喷漆绘制的涂鸦,宣称:“泰勒·德顿一直活着”…… 之后得克萨斯人才开始穿印着“拯救玛拉·辛格”的T恤…… 之后才出现各种未获授权的《搏击俱乐部》舞台剧…… 之后我的冰箱上才贴满陌生人寄给我的照片:鼻青脸肿却开怀大笑的面孔以及在后院拳击台上的格斗…… 之后这本书才以几十种语言出版:Club de Combate, De Vechtclub, Borilacki Klub, Klub Golih Pesti和Kovos Klubas…… 之后才有了所有这一切…… 其实原本不过是个短篇。不过是为了在工作时间消磨掉一个漫长的下午。我不想让小说里的角色从一个场景慢慢走到另一个场景,必须得找个办法大肆砍、砍、砍。要跳跃。从一个场景跳到另一个场景。不能让读者感到厌烦。要将小说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来,不过只留下每个方面的精髓。只要核心时刻。然后是另一个核心时刻。然后,另一个。 还得有种类似歌队的成分。有些平淡无奇,不会吸引读者的注意却能起到一种信号的作用:要往小说一个新角度或新层面跳了。这种平淡的缓冲部分将成为试金石或界碑,读者需要有这些东西才不会迷失在情节中。就像温和的果子露,在一次盛宴的各道主菜之前上的配菜。一个信号,就像电台节目的提头音乐,宣布下个节目即将开始。下次跳跃。 一种胶水或灰泥,可以将不同时刻和细节的马赛克拼成一个整体。给所有这一切一种连续性,又能突出每一时刻的重要性,避免它跟下一时刻搅和到一起,弄得两败俱伤。 想想影片《公民凯恩》吧,想想片中那个从未露面的无名新闻短片解说员,他是如何搭出一个框架,从众多不同的渠道来讲述那个故事的。 这就是我当时想做的。在办公室那个无聊的下午。 为了那个歌队——那个“过渡手段”——我列出了八条章程。整个关于搏击俱乐部的创意并不重要。那是可以随意胡思乱想的。不过那八条章程必须得有个安顿处,既如此,何不来一个你可以请人干架的俱乐部?就像你在一个迪厅里邀人跳舞一样。或者跟什么人玩一局台球或飞镖。搏击并非那个短篇的重点。我需要的是那些章程。有了这些平淡的界碑,我就有了充分的自由,既可以从过去也可以从现在,既可以从切近处又可以拉开距离描述这个俱乐部,既可以描述它的创立和演变,又可以将诸多细节和时刻捏合在一起——全部在七页之内——而且不会让读者厌烦。 当时我还有个乌青的眼圈没有褪尽,那是夏日度假时我跟人打了一架留下的纪念。没有一个同事问起过其中的缘由,我由此认识到,你在私人生活中尽可以做任何出格的事,只要带出来的伤够重,就没人想了解其中的细节。 与此同时,我还看过比尔·莫耶的一档电视节目,讲的是那些街头小混混,如何都是在父亲形象缺失的情况下被抚养长大的,他们都努力想相互帮衬着成为男人。他们发布命令和口令。强制执行章程和纪律。奖罚分明。跟教练或军事操练警官的所作所为毫无二致。 与此同时,书店里满坑满谷都是《喜福会》、《丫丫姐妹会的神圣秘密》和《如何缝一床美国棉被》。这些小说都展示了一种社会模式,女性可以藉此聚在一起。团团围坐,讲讲各自的故事。分享她们的人生。可从来没有一本小说为男性提供一种新的社会模式,让他们也可以分享他们的人生。 它必须为男人提供某种游戏或者任务的结构、角色和规则,但又不能过于卿卿我我。它必须创塑一种召集和聚会的新途径。它可以是“搭建谷仓俱乐部”或“高尔夫俱乐部”,而且它应该能够卖掉更多的书。毫无威胁性。 可是在那个漫长的下午,我却写了个七页纸篇幅的短篇小说,叫《搏击俱乐部》。这是我卖出去的第一个真正的短篇小说。一本叫做《追求幸福》的文选,由蓝鹭出版社出版,他们花五十块买下了它。可是这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人丹尼斯和丽尼·斯托瓦尔却把每本书书脊上的标题都印错了,重印的费用直接导致这家小出版社破产。如今,他们已经把所有的书都卖光了。不管是印对的还是印错的。我要跟那些想找那篇最早的短篇小说的人说一句,它的大部分已经变成了《搏击俱乐部》这本书的第六章。 它之所以只有七页篇幅,是因为我的写作老师汤姆·斯潘鲍尔曾开玩笑说,七页是一个短篇最完美的长度。 为了把这个短篇扩充为一本书,我把朋友们的所有故事都加了进去。我参加的每个派对都使我获得更多的材料。有迈克将色情镜头接到家庭电影上的故事。有杰夫做宴会侍应往汤里撒尿的故事。一位朋友曾表示担心,怕有人会依样画葫芦,而我则坚持认为我们都不过是住在俄勒冈、只能读完公立中学的蓝领鼠辈。我们根本无从想象,比如说一百万人还有什么事儿是没做过的。 多年后,在伦敦,一次签售活动前有个年轻人把我拉到了一边。他是家五星级饭店的侍应——城里总共只有两家五星级饭店——他爱死了我对侍应糟蹋食物的描写。读到我的书以前,他老早就跟别的服务生开始乱搞给名流上的菜了。 我要他报个名流的名字,他摇了摇头。不,他不敢说。 于是我就拒绝给他的书签名,他示意我靠近些,悄声告诉我: “玛格丽特·撒切尔吃过我的精液。” 他举起手来,五指分开,道: “至少五次……” 在我开始学着写小说的工作坊,你得公开朗读你的作品。大部分情况下是在酒吧或咖啡馆朗读,这样你就得跟蒸馏咖啡机的吼叫竞赛。或是电视上放的橄榄球赛。还有音乐和醉鬼的嚷嚷。面对所有这些噪音和分心的事儿,只有最骇人听闻,最暴力、黑暗和滑稽的小说才会有人听。这样的听众才不会安安静静地坐着听什么“搭建谷仓俱乐部”呢。 说实话,我当时写的不过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当代版。它是部“使徒式”小说——由一个劫后余生的使徒讲述他的主人公-英雄的故事。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其中一个男人,主人公,被枪杀。 这是个经典、古老的罗曼司,移植到了当代,来跟蒸馏咖啡机和ESPN 竞赛。 我花了三个月时间写出第一稿,然后在三天内卖给了W·W·诺顿出版公司。可预付金实在太可怜,我没好意思告诉任何人。谁都没告诉。只有六千美金。直到现在,别的作者才告诉我,这叫“礼退金”。他们给这么少的预付,是期望作者自觉受辱,主动退却。这样一来出版社就免了干系,不会得罪本来想出这本书的某位编辑。 不过毕竟是六千美金。这等于我一年的房租呢。我于是接受下来。于是在1996年八月,这本书出了精装本。还搞了个三地宣传活动——西雅图、波特兰和旧金山——在任何一地的任何一次图书朗读会上出现的读者都不足三人。图书销售抽的那点版税,都不够付我在酒店迷你酒吧里喝的酒账。 有位书评人把这本书叫科幻小说。另有一位把它称为对“铁约翰” 男性运动的嘲讽。另一位称其为对公司白领文化的嘲讽。有人称它为恐怖小说。没有一个人认为它是个罗曼司。 在柏克利,有位电台主持人问我:“您既然写了这本书,请问您对当今美国女性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何看法?” 在洛杉矶,有位大学教授在国立公共电台上说这本书写得不成功,因为它没有强调种族问题。 在回波特兰的飞机上,一位乘务员俯身凑近我,要我别卖关子跟他实话实说。他的理论是这本书根本就不是写什么搏击的。他坚称它写的其实是男同性恋们相互看对方在公共蒸汽浴室里捉对儿宣淫。 我跟他说,是呀,管它呢。于是在接下来的航程中他免费请我喝了好几杯酒。 另有一些书评人痛恨这本书。哦,他们说它“太黑暗”,“太暴力”,“太尖锐太刺目太独断”。他们还是喜欢“搭建谷仓俱乐部”去吧。 尽管如此,它还是获了1997年度“西北太平洋书商奖”,以及1997年度俄勒冈最佳小说奖。一年后,在南曼哈顿的KGB文学酒吧 里,有位女士主动跟我搭话,她自我介绍说她是俄勒冈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说她当时为了说服别的委员简直进行过殊死搏斗。愿上帝保佑她。 一年后,在同一个酒吧,另一位女士主动跟我搭话,自我介绍说她正在为电影《搏击俱乐部》设计那个电脑动画企鹅。 再后来,就是布拉德·皮特、爱德华·诺顿和海伦娜·邦汉·卡特了。 从那以后,成千上万人给我写了信,大部分都说“谢谢你”。因为我写的书让他们的儿子又开始阅读了。或她们的丈夫。或他们的学生。另有些人写信来略有些生气地说起他们是如何发明出搏击俱乐部这整套想法的。是在新兵训练营。或大萧条时代的劳改营。他们曾在喝了酒之后相互要求:“揍我。铆足了劲儿揍我……” 一直以来就有搏击俱乐部,他们说。而且搏击俱乐部会永远存在下去。 侍应总会往汤里面撒尿。人总会坠入情网。 如今,在我写了七本书之后,男人们仍在问我在他们附近到哪儿去找搏击俱乐部。 而女人们也仍在问我,是否有家俱乐部能让她们干一架。 如今,这成了搏击俱乐部的首要规则:一个住在俄勒冈、只能读完公立中学的蓝领鼠辈根本无从想象亿万人还有什么事儿是没有做过的…… 在玻利维亚的群山之中——那个地方还没出版过这本书,距离那位醉醺醺的牛仔和他那闹鬼地道之旅有几千英里之遥——每年,那些赤贫的乡民都会聚集在安第斯山高高的村庄里,庆祝“廷库”佳节 。 在那里,那些自耕农会相互把对方的屎都揍出来。醉意醺醺、鲜血淋漓,他们赤手空拳打得天昏地暗,一边高唱,“我们是男人。我们是男人。我们是男人……” 男人和男人对打。有时女人也相互对打。他们照着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方式厮打。他们的世界中几乎没有财富和财产,没有教育和机会,这个节日他们翘首以盼了整整一年。 然后,等他们打得筋疲力尽了,男男女女就一起去教堂。 去结婚。 累了并不等于富了,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庶几近矣。 · · · · · · (收起)文件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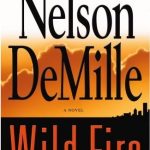




![龙族(第一部)之火之晨曦 [Kindle版]](https://dushuxiaowu.com/wp-content/themes/Git-alpha/timthumb.php?src=https://dushuxiaowu.com/wp-content/uploads/2021/11/68938180189c11ec9562b8098a44e5cd.jpg&h=110&w=185&q=90&zc=1&ct=1)
